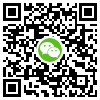我记得那是2024年秋天的一个下午,我作为一名律师,坐在调解室里,面对着一对即将离婚的夫妻——李女士和张先生。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紧张感,调解员试图缓和气氛,但两人的眼神却像刀锋般交错,似乎随时都会擦出火花。这不是一场普通的离婚诉讼,而是涉及子女抚养权、财产分割和一桩隐秘家庭暴力指控的复杂调解。我的任务是为李女士提供法律支持,同时确保调解过程不至于彻底失控。
李女士今年38岁,是一家公司的中层管理者,外表干练,但那天她的手却微微颤抖。她告诉我,结婚12年来,张先生从最初的温柔体贴,逐渐变得暴躁易怒,甚至在争吵时有过几次动手的行为。她没有报警,也没有留下明显的证据,因为“怕孩子看见,怕丢人”。直到半年前,她发现张先生不仅对她冷暴力,甚至开始私下转移夫妻共同财产,她才下定决心离婚。而张先生则坚称自己从未暴力对待妻子,指责李女士“无中生有”,是为了多分财产才编造谎言。
调解开始时,张先生率先开口,语气强硬:“我同意离婚,但孩子必须归我,房子是我婚前买的,她一分钱也别想拿走。”李女士低头沉默了一会儿,然后抬起头,声音平静却坚定:“孩子不能给他,他连自己都管不好,怎么养孩子?至于房子,婚后还贷的钱有一半是我出的,我有权分。”调解员试图打圆场,但双方各执一词,火药味越来越浓。
作为李女士的律师,我知道这场调解的关键不在于争吵,而是证据和法律依据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1079条,离婚调解是诉讼离婚前的重要程序,如果调解失败,法院将依法判决。而在这之前,李女士需要证明张先生的家庭暴力行为,以及她在夫妻共同财产中的合法权益。可问题在于,她没有直接证据——没有报警记录,没有医院诊断书,甚至连邻居的证言都拿不出来。她唯一能提供的,是几段手机录音,记录了张先生辱骂她的片段,还有银行流水显示她多年来为房贷和家庭开支的付出。
我建议李女士在调解中先从子女抚养权入手,因为这是她最关心的。根据《民法典》第1084条,离婚后不满两周岁的子女原则上由母亲抚养,除非有特殊情况。而他们的孩子才5岁,法院通常会优先考虑母亲的抚养能力。我提醒她冷静陈述自己的经济状况和工作稳定性,同时指出张先生长期加班、疏忽孩子的事实。果然,当李女士提到孩子因为张先生的忽视而在幼儿园频频生病时,张先生的脸色变了,他反驳说:“我忙是为了赚钱养家,她倒好,整天拿孩子做文章!”
调解员适时介入,要求双方提供抚养能力的证明材料。这时,我悄悄递给李女士一份幼儿园老师的书面证言,证明她平时接送孩子、参加家长会的频率远超张先生。这份证言虽不算决定性证据,但在调解中无疑增加了她的筹码。张先生显然没料到这一招,语气开始软化,但仍坚持房子是婚前财产,不愿分割。
关于财产问题,我向调解员提交了李女士婚后还贷的银行流水和工资单,依据《民法典》第1062条和第1063条,婚后共同还贷部分及其增值属于夫妻共同财产,应予分割。张先生辩称房子首付是他父母出的,属于个人财产,但当我追问他是否有赠与公证或书面协议时,他哑口无言。调解员皱着眉,翻看了我们提交的材料,低声与旁边的书记员说了几句。
就在气氛稍有缓和的时候,李女士突然拿出了那段录音。手机里传出张先生尖锐的辱骂声,甚至夹杂着摔东西的动静。调解室里瞬间安静下来,张先生的脸色苍白,试图解释那是“夫妻间的正常争吵”。我立刻补充道,根据《反家庭暴力法》第2条,家庭暴力不仅包括身体暴力,精神上的严重侵害也属于违法行为。这段录音虽不能直接作为刑事证据,但在离婚调解中足以影响抚养权和财产分割的判断。
调解进行了整整三个小时,最终在调解员的建议下,双方暂时达成初步协议:孩子归李女士抚养,张先生每月支付抚养费2000元;房子归张先生所有,但需支付李女士婚后还贷部分的补偿款15万元。至于家庭暴力指控,李女士表示暂时不追究,但保留日后诉诸法律的权利。张先生虽不情愿,却也知道继续僵持对自己不利,只得签字。
走出调解室时,李女士对我说:“谢谢你,我终于觉得能喘口气了。”我笑了笑,心里却清楚,这场调解只是她人生新篇章的开始。法律是冰冷的条文,但在每一个具体的故事里,它却是当事人争取公平的武器。那天的调解没有法庭上的唇枪舌剑,却充满了无声的较量,而我作为律师,见证了法律如何在生活的缝隙中,缓缓拨开迷雾。